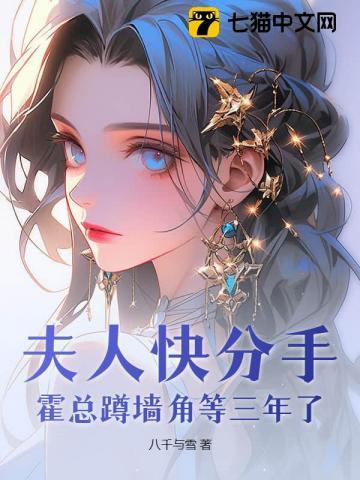乐文小说中文>无字史记(出版书) > 第4节(第2页)
第4节(第2页)
&esp;&esp;这批“海岸暴走族”的航海能力应该很强。澳大利亚大陆在上亿年前就与其他大陆分离了,大陆上的动物非常古老,在现代智人到达前,澳大利亚大陆上连灵长类动物都没有,当然也就不曾有过任何古人类。直立人之一的爪哇人曾经居住在距离澳大利亚大陆只有100千米的北方岛屿上,却只能望洋兴叹。即使在冰期海平面下降的条件下,从东南亚的岛屿跨海到达澳大利亚大陆,仍然要穿越惊涛骇浪,没有先进的航海工具和优秀的航海技术,是不可能做到的。
&esp;&esp;优秀的航海能力让“海岸暴走族”在抵达东南亚后,不仅向南到达了澳大利亚大陆,而且继续沿着海岸线向北挺进,而东南亚的北面,就是今天的中国。时间可能非常早,距今约5万年前,中国的海岸线就出现了现代智人的身影。令人遗憾的是,那时候的海岸线如今已经被海水覆盖了。
&esp;&esp;这批现代智人顺着中国东南部海岸一路向北,甚至抵达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在今东北亚和蒙古等地的现代人中,高达50的人拥有“海岸暴走族”的基因。这说明他们不仅喜欢在海岸线冲浪,而且曾经深入内陆地区,所以中国东北地区也是这批现代智人的途经之地。
&esp;&esp;也许是过于痴迷于海岸生活,不善于在内陆谋生,也许是大冰期控制的大陆内部过于寒冷,不适合当时的人类生存,这批现代智人留到今天的后代并不多。现代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来自另一批走出非洲的现代智人。
&esp;&esp;3万年前的猎人祖先
&esp;&esp;在距今5万年前,又一批非洲现代智人迈出了远行的脚步,他们踏着距今10万年前那批壮烈先辈的足迹,再次勇敢地跨过撒哈拉沙漠,朝北走向了西亚地中海沿岸。
&esp;&esp;人类史前历史掀开了新的篇章。
&esp;&esp;与早自己2万年出发的“海岸暴走族”不同,这批现代智人更擅长狩猎,比自己的祖先海德堡人更加优秀,我们可以称呼他们为“草原狩猎族”。考古学家发现,在距今6万—5万年前,远古人类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人造投射装置—轻型标枪和弓箭。这种远距离猎杀动物的武器提高了狩猎的效率,并降低了人类与猛兽直接搏斗导致的死亡率,这样,人口的增长率大大提高,出现了一次人口膨胀。可能也正是手握尖利的木制标枪与弓箭,使得这批走出非洲的现代智人“不屑于”沿着海岸线旅行,而是热衷于追逐大型动物走向西亚。
&esp;&esp;凭借新发明出来的弓箭,“草原狩猎族”发现欧亚草原带简直是人间天堂。绵延万里的欧亚草原带就是他们的“草原高速公路”,沿着草原带,他们迅速进入当时水草丰美、野兽成群的中亚地区。卓越的狩猎能力让他们能在仍然寒冷的大陆内部生存并壮大。然后,实力强大的“草原狩猎族”以中亚为基地,继续向四周扩散。
&esp;&esp;其中一支南下进入印度次大陆,当他们抵达印度海岸附近时,遇到了比自己早1万多年来到印度的“海岸暴走族”。即使经过了1万多年,“海岸暴走族”仍然人丁单薄,根本不是凶悍的“草原狩猎族”的对手。基因研究表明,“海岸暴走族”的女性融入了“草原狩猎族”的人群之中,而男性基本上都断绝了后裔。
&esp;&esp;难道“草原狩猎族”杀死了“海岸暴走族”的男人,抢走了“海岸暴走族”的女人?
&esp;&esp;这种可能性很大,远古不同人群之间的融合过程没有今日世界的人权、法律的束缚,当时流行的是“丛林法则”,这种杀死男人、抢走女人的事件,我们还会在接下来的人类历史中频频遇到。
&esp;&esp;“草原狩猎族”中的另一支沿着草原带一路向东,越过了长期隔绝东亚和中亚的天山、阿尔泰山等山系,进入蒙古和中国北方。从基因比例上看,东亚人群中有一半以上的现代人体内都有“草原狩猎族”的独特基因。他们抵达中国北方的时间可能在距今35万—3万年前。
&esp;&esp;在长达百万年的时间里,中华大地一直“门庭冷落车马稀”,除了在本地艰难挣扎的少量直立人部落,没有什么人气,几乎不见“来客”。在距今5万—3万年前,中华大地突然间变得热闹起来。这个时期,至少有两批现代智人—“海岸暴走族”“草原狩猎族”分别来到东亚,这里可能还存在着少量直立人和丹尼索瓦人,如果后面这两类人没被大冰期或现代智人消灭的话。
&esp;&esp;现代智人能够冲破地理阻隔,频频进入中华大地,一方面是由于自身更有智慧、技术能力更强,另一方面是由于“天时”配合,他们抓住了气候的有利时机。
&esp;&esp;中国的古气候透露了相关信息。对黄土高原沉积的古土壤里化学元素的分析结果表明,距今9万—6万年前气候寒冷,这段时期估计全球都处于寒冷时期,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现代智人抓住海平面下降的机会,沿着海岸线走出非洲,“海岸暴走族”展开了一轮大扩张。距今6万—25万年前,黄土高原处于相对温暖的时期,对应着现代智人向欧亚大陆迁移,“草原狩猎族”大扩张。距今25万—14万年前,黄土高原又变得异常寒冷。
&esp;&esp;另外,中国内蒙古西部曾经有一个很大的湖泊,叫作居延海。唐代诗人王维曾经写过一首《使至塞上》,诗云:“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里的“居延”就是指居延海。这首诗接下来的一句就更有名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说明唐代时居延海还存在,但是周边已经是大漠风光了。科学家从这个古湖泊的沉积物中的化学元素分析,湖水在距今37万—34万年前、距今31万年前左右、距今28万—26万年前的时段水位高,说明当时气候温暖湿润;在距今19万—14万年前的时段水位低,对应气候干旱(可能还有寒冷)。距今37万—34万年前这个温暖的“窗口期”,正是“草原暴走族”越过天山、阿尔泰山东进的时段。
&esp;&esp;如果对照古气候变化与现代智人扩张,我们就可以看出,现代智人在东亚的迁徙有一个“跷跷板效应”:当全球气候寒冷时,内陆冰天雪地,不适合人群居住和迁徙,而沿海海平面下降,适合人群生活和迁徙,于是南方的“海岸暴走族”及其后裔相对扩张;当全球气候温暖时,内陆春暖花开,适合人群居住和迁徙,沿海海平面上升,给沿海居住的人群带来麻烦,于是北方的“草原狩猎族”及其后裔相对扩张。
&esp;&esp;这个跷跷板效应能够让我们发现几万年以来现代智人在中华大地上的迁移线索,理解不同时段中国古人类的面貌。现在,让我们回到北京周口店,去亲密接触一下几万年前的现代智人祖先们。
&esp;&esp;“等等,你不是说周口店北京人并不是我们的祖先,他们在距今20多万年前就离开那里了吗?”
&esp;&esp;当然,距今几万年前,周口店已经没有了北京人,但是由于现代智人的扩张,他们也看上了龙骨山这块风水宝地,那里重新兴盛起来。
&esp;&esp;2001年,考古工作者在距离周口店北京人遗址6千米处的田园洞发现了包括下颌骨和部分肢骨在内的古人类骨骼和丰富的哺乳动物骨骼,这一古人类被称为“田园洞人”,几年后科学家根据骨骼内的化学同位素,确定田园洞人生活的年代在距今42万—385万年前。此后的基因检测表明,田园洞人属于现代智人,携带了极少量的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基因。
&esp;&esp;从生活时代看,田园洞人很可能是“海岸暴走族”沿着海岸北上后的后裔。虽然今天的周口店距离渤海海边有170多千米,但在几万年前,渤海湾的海岸线在今天津市的武清到静海一线,当时周口店距离海边只有100千米左右,从龙骨山向东南到达海岸边,基本上是一马平川,此后的海退以及河流沉积把海岸线向海洋方向推进了一大段。当年的“海岸暴走族”的后裔从海边到达周口店并不太难。
&esp;&esp;另一个可以间接支持田园洞人是“海岸暴走族”后裔的证据,来自南美洲丛林中的现代亚马孙人。基因对比发现,在美洲原住民各个人群中,只有亚马孙人与田园洞人的遗传关系最近。这意味着现代亚马孙人的古人类祖先可能与田园洞人关系密切。由于美洲人群都是从亚洲迁移过去的,如果只有田园洞人这一支现代智人迁入美洲,那么现代美洲所有原住民人群都应该与田园洞人的遗传关系密切。可实际情况是,只有远在南半球南美洲的亚马孙人与田园洞人遗传关系很近,很大可能说明与田园洞人亲缘关系很近的一支现代智人很早迁入美洲,后来又有其他现代智人进入美洲。考虑到“海岸暴走族”出色的航海能力,很早就扩张到东北亚地区,亚马孙人的祖先可能要追溯到“海岸暴走族”,因此田园洞人可能也是“海岸暴走族”的后裔。关于美洲人群的起源与扩张,本书将在后文详述。
&esp;&esp;基因研究还揭示,田园洞人可能并不是现代中国人的直接祖先,可能没有后代存活到今天。田园洞人最终断子绝孙了,这真是一个令人悲伤的消息。
&esp;&esp;似乎是要安慰我们寻根问祖频频受挫的心灵,龙骨山上的另一种古人类在田园洞人之后崛起于山顶的洞穴中,他们就是大名鼎鼎的山顶洞人。早在1933年,山顶的钟乳石山洞中就出土了古人类骨骼。也正是因为被发现得很早,山顶洞人的头骨原件和一些骨骼标本遭遇了和周口店北京人一样的命运,在战火中遗失了。
&esp;&esp;山顶洞人显然是心灵手巧的一类人,他们有大量的装饰品,穿孔的兽牙、海蚶壳、小石珠、小石坠、鱼眼上骨和刻沟骨管等。山顶洞人的骨器和装饰品制作得十分精美,他们已经掌握了钻孔技术﹐不仅会一面直钻﹐而且还能两面对钻。
&esp;&esp;山顶洞人的居住环境分成了几个洞室,科学家对里面的动物残骸进行了同位素测年,发现洞穴的上室和下室动物的生活年代分别是距今29万—24万前和距今34万—33万年前。由于这些动物应该是被山顶洞人猎杀的,因此这个时间也等同于山顶洞人的生活年代。
&esp;&esp;从山顶洞人的时段看,他们刚好生活在冰河时代相对温暖的日子里。由于科学家没能获得山顶洞人的遗传信息,因此无法通过分子生物学判断他们的祖先是谁、是否有后代存活到了今天。不过,他们有卓越的穿孔技术和骨针工具,这很可能是延续自“草原狩猎族”的东西,后者用骨针来缝制兽皮衣服。再考虑到山顶洞人的生活时代刚好在“草原狩猎族”东进之后,所以他们是“草原狩猎族”后裔的可能性很大,他们与比自己早1万多年来到周口店的田园洞人并不是一类现代智人。只是不知道两批智人是否曾经在龙骨山相遇。
&esp;&esp;“城头变幻大王旗”,龙骨山上古人类的更替,集中反映了几万年以来中华大地上古人类格局的风云变幻。在气候变迁这个幕后导演的指挥下,在自身人群生存压力的驱动下,不同人群在中华大地上南来北往,为了梦中的明天而持续奋斗(见表2–1)。
&esp;&esp;表2-1 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古人类
&esp;&esp;南下北上,走遍中国
&esp;&esp;从拥有的石器的种类看,以山顶洞人为代表的这批现代智人在当时的中华大地上广泛分布,至少从华北地区北部向南到黄河流域,都有类似技术和文化的古人类活动。我们今天所称的中原地区,是当时他们重要的活动区域,不同部落分布在平原的河谷地带,在水源和食物条件适合的地方安营扎寨,形成了较长时间居留的营地,并围绕自己的营地,在周边形成放射状的临时活动点,从事狩猎、采集,选取合适的石料加工石器。
&esp;&esp;有趣的是,考古学家在郑州南部发现了距今3万年前的古人类遗址,这批古人类远距离搬运来紫红色石英砂岩,专门垒砌成石堆基座,在上面摆放巨大的古棱齿象头,这种大象成年体重都在10吨以上。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出于对巨兽的恐惧或崇拜,还是通过仪式祈求狩猎丰收?
&esp;&esp;我们不得而知。这种类似于祭祀的活动,表明了当时的古人类有着丰富的精神世界。
&esp;&esp;山顶洞人的快乐时光大概持续了几千年到上万年,从距今约25万年前开始,全球进入了非常寒冷的时期,也就是“末次冰期盛冰期”。
&esp;&esp;科学家根据碳十四同位素信息,确定盛冰期的具体时限在距今265万—19万年,当时全球陆地约有14长年被冰雪覆盖,而今天全球陆地则只有110长年被冰雪覆盖。由于大量的地表水冻结成固态的冰,全球海平面比现在低100米甚至更多。从气温上看,盛冰期全球平均气温比现在低5~10c,在中高纬度地区甚至可能比现在低20c;在赤道地区,平均气温可能只比今天低2~3c,影响不大。酷寒的气候持续了7500年,直到距今19万年前,北半球大部分冰川才开始融化、退缩,盛冰期结束。
&esp;&esp;盛冰期中,中华大地也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距今27万—18万年前,陕西秦岭地区出现了云杉、冷杉林。这些树木生长在海拔近3000米、年平均气温25~57c的环境中,而今天秦岭一带年平均气温在13c,两相比较,距今约2万年前,秦岭地区气温比现在低7~10c。估计山顶洞人活动的华北地区也比今天低10c左右。由于气候变冷变干,生态环境恶劣,植物类型发生变化,乔木和木本植物减少,草本植物增加,其中的禾本科植物明显增加,而浆果类植物减少,人们的采集活动变得艰难起来。
&esp;&esp;盛冰期的到来,使得古人类的生存方式有了很大改变,反映在他们所使用的石器上,石叶、细石叶工具成为主流,这是适应干冷环境、频繁迁移、专业化的狩猎人群所使用的工具。在这段最寒冷的时光中,即使山顶洞人的后裔还活着,他们也应该不会继续在华北北部的龙骨山居住,他们可能向南迁徙了。说不定当时也有很多原本生活在欧亚草原带的“草原狩猎族”的后裔,为了躲避严寒向南迁徙而来,进入中华大地,生活在中原地区甚至更加靠南的区域。南方毕竟要暖和一点儿,食物稍微丰富一点儿。他们就如同中国历史上那些草原游牧部落一样,在气候变冷的时候频频南下,只不过他们的时代早了2万年,他们也还没有学会骑马,只能依靠步行。他们的南迁可能也不像后来的游牧部落南下那样战火纷飞,因为距今2万年前的寒冷时期,大地上本来也没有多少人群了。
&esp;&esp;总之,在盛冰期的时代,很可能发生过古人类从中国北方地区南下的迁徙事件。这是一段古老祖先群体的萎缩期,尤其是对古老的北方人群来说。
&esp;&esp;那么,在山顶洞人以及之后的盛冰期这段时光中,中国的南方地区是什么景象呢?
&esp;&esp;就在山顶洞人及其伙伴于距今3万年前在中国北方扩张之时,中国南方也并不平静。
&esp;&esp;我们知道,东南亚地区很早就有“海岸暴走族”生活,他们的后裔在那里养精蓄锐;从中亚进入南亚的“草原狩猎族”,也在四处扩张,他们的后裔进入东南亚地区,使得东南亚地区有着各种类型的人群,或者按照分子生物学家的说法,那里生活着各种基因型的人群。
&esp;&esp;借助温暖的气候,这些人群纷纷开始“北伐”,涌入中国南方地区。他们进入中国的路线可能有两条:一条就是通过“海岸高速路”,从华南地区深入内陆;另一条可能是从东南亚腹地顺着河流北上,进入今天的云南地区。分子生物学家发现,缅甸的现代人群中有很多古老的基因型,这些基因型也出现在中国西南地区的现代人群中,这说明两个地区有人群的交流。通过分析基因,学者们大概可以判断,在距今25万年前或更近的时段,有古老人群从缅甸向北迁入中国境内。
&esp;&esp;分子生物学家通过综合各地现代人群的y染色体和线粒体dna的数据,从父系遗传和母系遗传两条线索追溯现代智人在中华大地的扩张情况。他们发现,一部分y染色体的基因型与一部分线粒体dna的基因型的分布十分相似,而另一部分y染色体的基因型与另一部分线粒体dna的基因型的分布十分相似,可以分别用组合1和组合2来代表这两个基因型人群,其中组合1在北方现代人群中比例很高,组合2在南方现代人群中比例很高。而且,由于两种组合有大致相等的基因多样性,因此可以判断,分别携带这两种组合的古老人群基本上同时进入中国境内。
&esp;&esp;令人惊讶的是,这两种组合的人群并不是分别从北方和南方进入中国境内的。分子生物学家发现,他们都是从南方进入中国,然后逐渐向北扩张的。只是组合2在南方地区扩张得比较早,因此很多南方现代人群中拥有这种基因型组合。组合1进入中国境内,在迁徙到北方地区后才开始大肆扩张,因此很多北方现代人群中拥有这种基因型组合。
&esp;&esp;真正来自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地区的基因型,也就是从欧亚草原带南下的古老人群的基因,在今天的现代人群中所占比例很小。那些在盛冰期南下中原的古老北方人群,那些山顶洞人的伙伴,他们的命运可能不容乐观。
&esp;&esp;让我们猜测一下熬到了距今19万年前盛冰期结束后,中华大地上的古老人群的迁徙情况吧。
&esp;&esp;在盛冰期的打击下,北方古老人群损失惨重,这不仅意味着他们的人口和部落数量大幅减少,还意味着他们丧失了很多特有的基因型。就像在地球历史上的很多次生物大灭绝事件一样,盛冰期也会造成许多古老人群的灭绝。盛冰期时南方古老人群受到的打击较小,他们的人口、部落以及基因型的多样性远比北方更多。当盛冰期结束,一个相对温暖的时期来临时,人丁兴旺的南方古老人群纷纷开始“北伐”,向正在回暖的中原地区甚至更北方挺进。chapte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