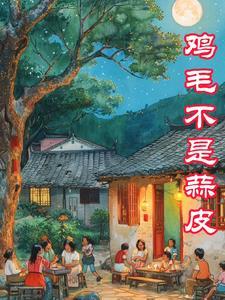乐文小说中文>无字史记(出版书) > 第5节(第2页)
第5节(第2页)
&esp;&esp;你看,我们仍然生活在由黍厘定的世界之中。
&esp;&esp;另一种起源于中国北方的重要农作物是菽,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大豆。与粟、黍这样的谷物粮食相比,菽胜在富含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相同质量的大豆的蛋白质含量是前两者的六七倍。与其他豆科植物类似,大豆的主根和旁根上生有根瘤菌,能够利用空气中的氮元素合成蛋白质。因此,大豆对于狩猎获得动物蛋白不足的古代人群具有非凡的意义,起码他们能够从大豆中获得大量植物蛋白作为营养补充。
&esp;&esp;菽的驯化可能比粟还要晚,驯化的时间、地点还没有搞清楚。野生大豆广泛分布于从东北大兴安岭到西南云贵高原的地区。在甲骨文中,出现了“受菽年”与“受黍年”同时占卜的现象,说明古人对这两种农作物的种植和收获季节相近,暗示了菽可能与黍的驯化区域相近。因此有学者推测,在北方的燕山山脉附近的山地、盆地等光照好的区域,可能是栽培大豆的起源地。
&esp;&esp;到距今约4000年前,中国北方的辽河流域、黄河流域乃至南方的长江流域,都出现了由野生大豆驯化而来的栽培大豆。之后甚至还产生了原始榨油的技术,说明古人已充分认识到了大豆的营养价值。
&esp;&esp;黍、粟、菽都起源于中国北方,它们的读音甚至都很接近,这不禁让人猜想,这样的读音在远古时代可能是古代人群对于可食植物或植物籽粒的一个统一的称呼,随着这些植物依次被驯化,它们的读音才略有分化。
&esp;&esp;在新仙女木期及之后出现的温暖期,“环球同此凉热”,欧亚大陆的气候变化可能是类似的。因此,在中国北方驯化出可以填饱肚子和增加营养的黍、粟、菽后,农作物迅速地从中国向外传播。
&esp;&esp;英国考古学家在距今约7000年前欧洲地区从黑海西岸到东欧和中欧的20多个不同地点,都发现了黍的遗迹。毫无疑问,这是中国驯化的黍向西传播的结果。
&esp;&esp;粟的传播紧跟黍的脚步,欧洲地区发现的最早的粟的实物证据的年代在距今5000年前,在距今3000年前粟的种植有明显增加。粟可能是通过欧亚大陆的草原带,经过今天的黑海沿岸进入欧洲的。粟还向东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比如韩国的一处遗址出土了粟,经过年代测定,距今约4500年;日本北海道距今4000年前的遗址中也出土了粟。粟甚至向西南传播到了遥远的古印度。有语言学家发现,古印度梵文中的粟的读音“cake”,也用于指代中国。粟可能是通过中国西南的横断山区的河谷,经过喜马拉雅山南麓走廊传播到古印度的。
&esp;&esp;所以,黍和粟不仅填饱了中国北方古人的胃,还填饱了广大欧亚大陆乃至周边岛屿上的人们的胃。既然民以食为天,有了充足的粮食才有文化与文明,那么中国的黍和粟的西传,算不算5000多年前东亚对于西方文明的巨大推动呢?
&esp;&esp;水稻:亚洲的第一缕米饭香
&esp;&esp;东亚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怎么能少了南方古人的智慧结晶—水稻?
&esp;&esp;关于水稻的起源地曾经众说纷纭。最早关注这个问题的西方学者发现,西方各种语言中“稻”这个词汇的源头来自印度梵文,而印度恰好是野生水稻分布比较多的地区,因此他们猜测印度是水稻的起源地。随后东南亚和中国境内也发现了大量的野生水稻,学者们的视线又转移到这些地方。20世纪50年代,学者们提出水稻最初的驯化地点可能在东南亚,因为那里动植物种类繁多,有大量的野生水稻可以用于筛选和杂交试验。
&esp;&esp;以上观点都受到了质疑。正如我们前面谈到的原理,自然环境优越、生存压力小的区域,不会是农作物诞生的首选地。南亚和东南亚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从事渔猎采集的古人没有太大的动力去驯化植物,并从事更为辛苦的农耕。只有在农作物经过漫长驯化,产量已经足够高后,传播到这些地区,那里的古人才有动力去种植。
&esp;&esp;不论是从理论探讨,还是实际的考古挖掘,最终学者们探索水稻起源地的目光投向了中国的长江流域。20世纪90年代,考古学家在湖南北部发现了城头山遗址,遗址附近发现了距今约8000年前的人工栽培稻,以及稻田的遗迹,遗迹中有水坑和水沟等原始灌溉系统,这可能是灌溉设施完备的最早水稻田。
&esp;&esp;此后的考古发现更加令人振奋,在江西北部仙人洞、吊桶环遗址,发现距今12000年前的野生稻植硅石和距今10000年前的栽培稻植硅石证据,说明上万年之前那里的古人就在进行水稻的驯化活动。2004年在湖南的玉蟾岩遗址,还发现距今18万—14万年前的驯化水稻的证据,这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稻谷遗存。
&esp;&esp;所以,如今的学者们基本认定,中国南方是水稻的起源地。
&esp;&esp;栽培水稻主要分为两大类—籼稻和粳稻。籼稻适合生长于南方湿热地区,今中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以种植籼稻为主;粳稻适合生长于北方干凉地区,今中国黄河流域以及更北方的东北地区,是粳稻的主要产区。植物学家通过水稻的基因分析,认为最早出现的水稻是粳稻,比如在浙江河姆渡遗址中发现的距今7000年前的古水稻,经过基因对比,与绝大多数粳稻基因接近,说明我们的南方古人最早是吃粳稻的,也就是类似今天东北大米的原始品种。稍后,很可能是在古印度的恒河平原,开始了籼稻最初的驯化过程,当地距今7000—5000年前的遗址中出土了古人消费稻米的证据;然后,中国的粳稻品种传播到了古印度,与原始的籼稻进行了杂交,改良了后者,使籼稻最终完成了驯化过程。
&esp;&esp;与北方黍和粟的漫长驯化过程类似,南方的水稻也经历了数千年的驯化过程。今天的江浙地区是中国古代早期文明的诞生地之一,那里的水稻驯化体现了古人与水稻之间相互依赖、协同发展的历史。
&esp;&esp;距今约10000年前,浙江有一个上山文化,植物学家从遗址里筛选样品,仅仅发现了两粒炭化的米。不过在当时古人制作陶器的陶土里发现了掺入其中的稻壳,古人把稻壳加入陶土中,可能是为了减小陶土的黏性,以免烧制时陶器破裂。从他们制作陶器的工艺以及焚烧稻壳的灰烬遗迹中,我们可以推测,在万年之前,水稻对于那里古人的生活已经不可或缺,他们不仅采集水稻籽粒,而且还对稻壳加以利用。
&esp;&esp;不过在上山遗址中并没有发现明确的农耕工具,那里出土的一些大石片,能够当成石刀或者石镰使用,可以收割田野里的野生水稻。古人可能也开始了耕种水稻的尝试,只是这种活动可能还比较原始。
&esp;&esp;上山文化之后,距今7000—6000年前,浙江东部平原上的河姆渡文化兴起,植物学家在不同的遗址中找到了大量的植物遗迹,里面就包括水稻籽粒。植物学家对发现的水稻籽粒进行了鉴定,发现在河姆渡文化早期,即距今6900年前,栽培水稻所占的比例不到30;到距今6600年前,栽培水稻所占比例接近40。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古人正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水稻种植水平,但是在当时,他们的栽培水稻还无法取代野生水稻。
&esp;&esp;当时与水稻竞争食物地位的植物很多,考古学家在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其他可食用的野生植物,如菱角、栎果、芡实、柿子、猕猴桃等,特别是富含淀粉且容易储藏的栎果。遗址中有很多栎果的储藏坑。这说明距今6000多年前,水稻农业还不发达,水稻只是古人的粮食之一,产量并不高。
&esp;&esp;中华大地什么时候才算真正进入水稻社会呢?
&esp;&esp;浙江余杭,一座宏伟的良渚文化城池展现在世人面前。这座巨大的古城内外共有三层:外面一层是外郭,面积达8平方千米;向内第二层是内城,面积约3平方千米,城墙周长68千米,墙基宽20~145米,全部用大卵石堆叠而成,墙体则用黄土堆积;内城的中心是宫殿,宫殿基址是一个规整的长方形高台,台高约10米,东西长达670米,南北宽达450米。在这座城池外面的北方和西北方,古人用11条草裹泥包垒砌的防洪大坝,构筑了大型的水利工程,保护着城池免受洪灾侵扰。
&esp;&esp;这座城池揭示了江浙地区一个高度发达的古老文化—良渚文化。
&esp;&esp;良渚文化广泛分布在环太湖地区,年代为距今5200—4300年前。考古学家明显感觉到,那个时期江浙一带的文化遗址数量大增,反映出人口大幅增长。发掘良渚古城的考古学家估计,仅修建古城中心的莫角山高台、内城墙和外城墙以及周围的大型水利工程,就需要约1200万立方米的土方量。如果简单地以每人每天1立方米的土方工作量计算,大约需要33万人不间断地劳作一年。如果按照1万人每年劳作200天计算,整个工程建设时间需要6年多。
&esp;&esp;一个5000年前的古代社会要完成如此巨大的工程量,必须有足够多的劳动工人,而且还要有大量的粮食和其他生活用品的供给,这就需要非常多的农业人员和手工业人员。
&esp;&esp;只有发达的农业,才能支撑良渚文化和良渚古城崛起于东方。良渚文化的根基,正是稻作农业。
&esp;&esp;植物考古的新发现证实了良渚文化时期稻作农业生产水平的高速发展。例如,属于良渚文化的茅山遗址古稻田,由灌溉水渠和田埂分割成长条形田块,每个田块面积1000~2000平方米不等,古稻田总面积达56000平方米,折算为84亩。再如,人们在莫角山高台边缘发现了一个大型灰坑,坑内出土了数量惊人的炭化稻米,估计原本是一处储存粮食的粮窖,后来发生了火灾。经过测算,粮窖内的炭化稻米在未被炭化之前的总质量约达13吨。从位置上看,这个粮窖可能是上层人物的仓储,这次火灾真是损失惨重。
&esp;&esp;良渚文化的繁荣,表明中华大地经过漫长的水稻筛选和栽培过程,在距今约5000年前终于进入了稻作农业阶段,水稻成为当时良渚社会的主导粮食品种。南方古人以稻米作为他们的主粮,并辅之以其他动植物食物。
&esp;&esp;水稻起源于中国南方,以此为中心向外辐射,向南传入东南亚和南亚,向东被先民们携带渡海,进入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其实,水稻在长江中下游与钱塘江流域驯化的过程中,就开始向四面八方传播了。考古发现,最迟在距今7000年前,水稻种植就已经越过黄河流域,在黄河下游地区扎下根来。到距今5600年前,水稻甚至打入了北方农作物黍和粟占据的陕西关中地区,那里的古人形成了黍、粟、稻兼作的种植模式。
&esp;&esp;水稻也是本章开头提到的贾湖遗址古人的食物来源之一。贾湖遗址中筛选出了大量的炭化植物籽粒,其中就包含水稻籽粒,总计有400余粒。这说明在今河南中南部这样的中原地区,古人已经借鉴长江流域的经验,尝试采集和种植水稻。
&esp;&esp;作为八九千年前的古人,贾湖古人的粮食获取方式与南方的河姆渡古人比较像。贾湖遗址出土了许多菱角、莲藕、栎果、大豆等。但贾湖古人能够悠闲地吹奏骨笛,还要归功于他们卓越的渔猎能力。贾湖遗址也出土了大量的鱼骨和软体动物甲壳,这说明他们的渔业很发达。考虑到他们的植物性食物还包括莲藕和菱角等水生生物,可以推断贾湖古人的生活方式应该是“靠水吃水”,当时他们的生活环境中水面应该很大,可以给他们提供大量的水生动植物资源。
&esp;&esp;别忘了,贾湖骨笛可是用丹顶鹤的翅骨制作的,丹顶鹤也喜欢在河湖边起舞弄清影呢。
&esp;&esp;贾湖古人的生活一定是很惬意的,至少在很多岁月里是食物比较充足的,这不仅让他们“仓廪实而知礼节”,创造吹奏艺术愉悦自己,还让他们可以用多余的粮食饲养家畜,比如猪,另一种起源于古老中国的食物。
&esp;&esp;猪和狗:古人最好(吃)的朋友
&esp;&esp;中国古代最早的家猪骨骼就是在贾湖遗址出土的,可能在距今8500年前,贾湖古人就开始饲养猪、吃猪肉。从狩猎自然界里的野猪到饲养家猪,同样是漫长的过程,古人需要跨过几个关键的门槛。
&esp;&esp;驯化野猪,首先是出于对肉食的需求。古人长期依赖狩猎为生,已经习惯了吃肉,吃的可能主要是鹿肉和野猪肉。随着他们的人口增长,在某个地区长期居住,周边的大型动物被大量猎取后,通过狩猎已经无法满足古人吃肉的需要了。于是,古人捕捉到幼小的野猪后,尝试把它们养大后再杀掉吃肉。其次,古人必须有足够多的粮食,除了满足自己的粮食需要外,还有一定的剩余,可以用于饲养家猪。这就意味着古人的农作物种植技术已经足够高超,能够稳定地达到相当多的产量。因此,驯化野猪必然是在农业得到一定发展后才出现的。此外,猪是一种杂食动物,对饲料的要求不高,这也是古人能够很早驯养猪的重要原因。
&esp;&esp;考古学和遗传学的证据都表明,东亚地区的古人曾经进行过驯化野猪的活动,而且可能还不止一次地驯化。北方以贾湖遗址的家猪为代表,南方以稍晚一些的跨湖桥遗址的家猪为代表,似乎表明中华大地在距今8000年前分别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出现了家猪饲养。
&esp;&esp;动物学家采集了很多黄河流域的古代猪的基因样本,分析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结果发现,黄河流域的古代猪可能是从单一的驯化中心起源的,考虑到黄河上游地区的家猪驯养晚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可以推断北方家猪的起源地可能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也就是包括贾湖遗址在内的中原地区。在距今8000多年前驯养家猪后,黄河流域兴起了养猪热潮,到距今6000多年前,家猪提供的肉食在古人肉食资源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甚至可以占到80。
&esp;&esp;养猪是门大学问。北方古人在养猪方面的经验也是不断积累的。从遗址中的猪骨分析发现,在距今8000年前,被宰杀的猪大概在半岁到一岁,古人急于吃掉小猪;到距今4500年前,被宰杀的猪都在一岁或者更大一些了。在当时的饲料条件下,养到一岁的家猪的产肉率是最高的,也就是饲料转化率高,而年幼的猪长肉太少,年长的猪长肉变慢,都程度不等地浪费了饲料。
&esp;&esp;那么,当时的家猪会与人类“争食”吗?它们骨骼里的碳同位素透露了相关信息。古人靠采集获得的植物性食物,很多都是所谓的碳三植物,而靠种植获得的粟和黍等食物,是碳四植物。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一处遗址中出土了人骨和猪骨,科学家通过分析发现,当时的人和猪都吃大量的碳四植物,所以人和猪都是以粟、黍为食的。更大的可能是,人吃小米和黄米,喝小米和黄米酿造的酒;猪吃小米和黄米的谷壳,还有糟糠—酿酒剩下的残渣。
&esp;&esp;但是在长江流域,家猪并没有得到古人的追捧。虽然在距今7000多年前南方古人也开始饲养家猪,但他们似乎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养猪,没有把养猪当成生活中的重要事项。在距今7000多年前到距今5000年前的南方古人的遗址中,出土家猪的数量始终很少,他们的肉食需求主要依靠捕获鹿这样的野生动物来满足,或者捕捞河湖中的鱼类、贝类进食。在距今5500—5100年前的长江三峡一处遗址中,墓葬中的一位女性的双臂下面各放了一条大鱼,鱼长半米左右,几乎与死者的手臂一样长。这种以鱼作为随葬品的现象并不少见,说明当时的南方古人更为注重鱼类资源。饲养家猪,很可能也有丰富饮食的因素在里面,并不完全是因为肉食缺乏。
&esp;&esp;5000年以前古老中国“南鱼北猪”肉食格局的形成,应当是自然环境造成的。北方的河湖比南方少,而且冬季会结冰,因此黄河流域的鱼类资源相比长江流域少很多。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北方古人对黍、粟的驯化较为成功,粮食产量上来了,而同时期南方古人对水稻的驯化还在路上,粮食没有太多剩余,因此影响了南方养猪活动的发展。
&esp;&esp;不过“南鱼北猪”肉食格局随着良渚文化的崛起而一举改变了。在良渚文化遗址中,家猪骨骼在出土的动物骨骼中突然占据了多数,这说明良渚古人进行了长时期、大规模的养猪活动。良渚文化兴旺的稻作农业给养猪提供了饲料基础。良渚古人如此热衷于养猪,说明他们有大量的人口聚集在居住点附近,从良渚古城巨大的工程量就可以推测,大量的管理人员和劳动人员长期聚集一处,周边环境已经无法提供足够的肉食,依靠捕捞鱼类和贝类满足不了人们的需要,所以才选择了饲养家猪。
&esp;&esp;在远古时代,良渚文化其实是南方地区的一个特例,是在南方水乡泽国的环境中一次“人定胜天”的史前时代大跃进。良渚古人最大限度地种植水稻,获得尽可能多的粮食,养活大量的人口,并饲养家猪作为肉食改善营养,以完成巨大的建筑工程。
&esp;&esp;他们如此热衷于建设城池、房屋和水坝,是与他们神秘的信仰相关的。考古学家从良渚文化中能够感受到良渚古人有着较为狂热的信仰,他们不想建设什么威震四方的“王国”,而是梦想建设一个地上的“天国”,信仰驱动着他们执意要超越自身的时代,登峰造极。
&esp;&esp;所以,良渚文化有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悲壮感。从良渚文化衰落后当地兴起的马桥文化来看,长江流域、钱塘江流域的南方古人又恢复到了良渚之前的文化状态,以捕鱼和打猎作为自己获得肉食的方式,他们几乎不再养猪,不再雕琢精美的玉器,他们的社会结构比良渚文化简单得多,就好像良渚时代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南方地区再现类似于良渚文化这样的“巅峰时刻”,恐怕要等到春秋时期的吴越争霸时了,那是公元前500年前后,距离良渚文化衰落已经过去了约1800年。chapte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