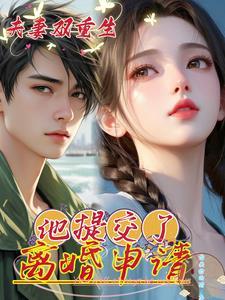乐文小说中文>1937年的日子 > 第29章 铁火熔新刃星火照山河(第1页)
第29章 铁火熔新刃星火照山河(第1页)
铁火熔新刃,星火照山河
一、山洞工厂的铁皮屋顶
惊蛰刚过,狼牙山深处的积雪还没化透,山洞工厂的入口却已经热闹起来。李明远踩着冻硬的泥地,看着工人们正往洞口架铁皮——那是从日军炸毁的火车上拆下来的废铁皮,被铁匠们敲平了,要搭个遮雨的屋顶。
“李队长,铁皮够了!就是钉子不够,木楔子得用硬木,山里的桦木不经砸。”老铁匠王师傅抹着汗喊,他手里的铁锤还在叮叮当当地敲着,火星溅在冻地上,瞬间熄灭。
李明远弯腰捡起块碎铁皮,边缘锋利如刀。这是他们的“厂房”:天然山洞改造成的车间,石壁上凿着粗糙的搁板,架着缴获的机床——两台日式车床,是上次伏击运输队的战利品,被机械师老张拆了又装,勉强能用。
“钉子的事我来想办法。”李明远拍了拍王师傅的肩膀,转身往山洞深处走。洞里比外面暖,弥漫着机油和煤烟的味道,二十多个工人散落在各处,有的在打磨枪管,有的在组装手榴弹,叮当声、敲打声混在一起,像粗粝的歌。
“队长!”机械师老张举着个零件跑过来,脸上沾着黑油,眼里却亮,“你看这个!按你画的图改的撞针,试过了,三八大盖的子弹能通用,击率提高了三成!”
那是个黄铜零件,边缘被打磨得很光滑,与老张满是老茧的手形成鲜明对比。李明远接过来看了看,图纸上的线条还在脑海里清晰着——那是他穿越前在军工博物馆见过的改良型撞针结构,没想到真能在这简陋的山洞里做出来。
“好。”他点头,“让学徒们照着这个多做几个,下午试装到步枪上。”
老张咧嘴笑:“得嘞!就是……铜料快没了,上次收的废铜都用完了。”
李明远皱了皱眉。根据地缺料是老问题,铜、铁、钢材全靠缴获和百姓捐献,有时候连弹壳都要捡回来复装。他走到山洞尽头的木板桌前,铺开一张画满线条的纸,上面是个奇怪的装置,像个缩小的水车,却带着齿轮。
“这是啥?”通讯员小周凑过来,指着图纸上的“风车”问。
“水力冲压机。”李明远用笔在上面圈了个齿轮,“山涧的水流能带动它,比人砸省力,冲压弹壳效率能提五倍。”
小周咋舌:“队长,你咋啥都会画?这玩意儿真能成?”
李明远笑了笑没说话。穿越前他是机械工程系的研究生,宿舍床底下堆的全是武器模型图纸,没想到这些“不务正业”的爱好,如今成了保命的本事。他手指在图纸上划过,从步枪改良到手榴弹引信,从水力冲压机到简易炼油装置——这些在现代看来基础的技术,在缺医少药、物资匮乏的根据地,却是能救命的宝贝。
“小周,把这张图送到后勤处,让他们组织人去山涧测量水流落差。”李明远把图纸折好递给他,“告诉王主任,就说急需一批硬木和铁条,木楔子要用来固定机床,铁条做冲压机的传动轴。”
小周刚跑出去,负责后勤的老郑就喘着气进来了,手里抱着个布包:“李队长,好消息!山下李家庄的百姓捐了一批东西,你快看看!”
布包打开,里面是些铜勺、铁犁、旧马蹄铁,甚至还有个黄铜烟袋锅。老郑红着眼圈说:“王大爷说,家里就这些能砸的铁了,让咱多造点枪,早一天把鬼子打跑。”
李明远拿起那个烟袋锅,铜皮被摩挲得亮,还带着烟火气。他攥在手里,沉甸甸的,像攥着一团滚烫的血。
“告诉乡亲们,这些东西我都记下了。”他声音有些哑,“让铁匠班先把烟袋锅熔了,做撞针够好几个了。”
老郑点头要走,李明远又叫住他:“对了,让炊事班多蒸两锅窝头,晚上给工人们加个菜——就用上次送来的土豆,炖一锅。”
山洞里的叮当声还在继续,李明远望着石壁上摇曳的油灯,突然觉得,这简陋的山洞,比他穿越前见过的任何现代化工厂都要珍贵。这里没有精密的仪器,却有最坚韧的人;没有充足的材料,却有源源不断的心意——从百姓捐来的铜烟袋,到工人磨出血泡的手,都在告诉他,这不是空想,是能落地生根的希望。
二、图纸上的“未来”
夜深了,山洞工厂的工人大多休息了,只有李明远的“办公室”还亮着油灯。那是个凿在石壁里的小隔间,摆着张木板桌,上面堆着厚厚的图纸和几本书——《机械原理》《化工基础》,都是他穿越时塞进背包的教材,书页边缘已经磨卷了。
他铺开一张新图纸,笔尖蘸着自制的墨汁(用锅底灰和桐油调的),开始画一个奇怪的武器。不是步枪,不是手榴弹,而是个带着支架的筒状物,筒身上画着刻度,底部标着“底座加重”“尾翼稳定”的字样。
“这是……迫击炮?”门口传来动静,老张端着碗热水站在那里,眼睛瞪得溜圆。
李明远没抬头:“算是吧,简化版的。”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这是他根据记忆画的毫米迫击炮图纸,去掉了复杂的瞄准系统,用最简陋的材料就能仿制。日军的迫击炮总在战场上压着他们打,他要造出属于根据地的“小炮”。
老张凑过来,手指在图纸上点着:“这玩意儿能打多远?比咱的土炮准吗?”
“保守说,能打两公里。”李明远在炮筒下方画了个三角形支架,“瞄准靠这个标尺,简单易操作,新兵练三天就能上手。”
老张吸了口凉气:“两公里?那鬼子的机枪阵地,咱在山后头就能端了!”
“不止这个。”李明远翻出另一张图纸,上面画着个长方体的铁盒子,侧面有个插销,“这个是集束手榴弹,五个捆在一起,加个延时引信,能炸掉日军的碉堡。”
他又抽出一张画着齿轮和链条的图纸:“还有这个,脚踏式电机,能给电台供电,不用再靠手摇,省人力。”
老张看得眼睛直,手指在图纸上轻轻摸着,像在触摸什么稀世珍宝:“队长,你这脑子是咋长的?这些东西……真能做出来?”
“能。”李明远肯定地说,“迫击炮的炮筒用铁轨钢锻打,咱山里有废弃的铁轨;电机的齿轮用硬木削,链条可以用马车上卸下来的旧链条改造。难的是工艺,得让铁匠们练淬火,炮筒不能有沙眼,不然会炸膛。”
老张搓着手,激动得直转圈:“我这就去跟铁匠班说,让他们连夜练!王师傅以前在县城铁铺做过犁头,淬火他懂!”
“别急。”李明远叫住他,“还有更重要的。”
他从书里抽出一张单独的图纸,上面画的不是武器,而是个螺旋桨一样的东西,旁边标着“抽水机”“灌溉用”。
“这是啥?”老张纳闷。
“给地里浇水用的。”李明远解释,“用风力或者水力带动,比人挑水快十倍。等打完仗,咱不光要造武器,还得造这些东西,让地里多打粮食,让乡亲们能吃饱穿暖。”
老张看着图纸上的抽水机,又看看外面黑沉沉的山,突然叹了口气:“以前总觉得,能把鬼子打跑就不错了,没想到……还能想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