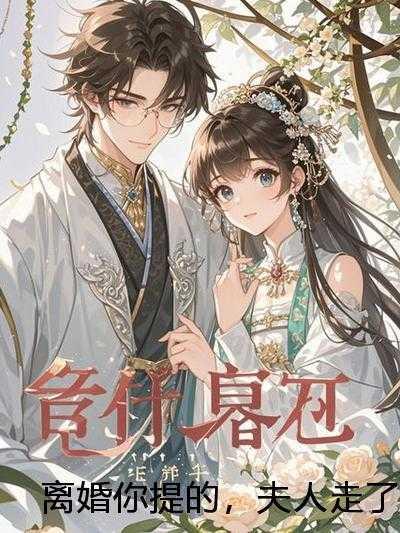乐文小说中文>1937年的日子 > 第46章 利器锋芒初现世单兵重器破敌锋(第1页)
第46章 利器锋芒初现世单兵重器破敌锋(第1页)
第四十六章:利器锋芒初现世,单兵重器破敌锋
一、兵工厂的“硬骨头”:火箭筒研的百次淬炼
黄土岭战役结束后,李明远带着赵刚、周先生钻进了兵工厂的试验所。地上摊着被炸毁的日军坦克残骸,履带断成几截,装甲板上的弹痕深浅不一。李明远指着一块布满凹坑的装甲板,声音沉得像块铁:“你看这上面的弹痕,都是战士们用炸药包拼出来的。咱不能总让弟兄们抱着炸药包往坦克底下钻,得搞出能在几十米外打穿铁甲的家伙。”
周先生的手指抚过装甲板上的裂纹,忽然眼睛一亮:“老李,我想起个东西——德国人的‘铁拳’反坦克榴弹射器,上次晋察冀的同志提过,说是能扛在肩上打,专门对付坦克。咱能不能仿一个?”
“仿!”李明远一拍桌子,“不管是啥法子,能让战士们少流血,咱就干!”
可仿制的难度远想象。“铁拳”的原理不复杂:用一根铁管当射筒,里面装射药,前端装破甲榴弹,点燃射药后,榴弹能飞几十米,击中目标后靠聚能装药炸开装甲。但难就难在“聚能装药”的配方和射筒的密封性——装药配方不对,炸不开装甲;射筒漏气,榴弹飞不远,还可能炸伤自己。
周先生带着五个工程师、二十个老工人,在试验所里搭起了简易车间。没有图纸,就凭着晋察冀同志的描述画草图;没有专用钢材,就用缴获的日军炮管切割后打磨;没有精密量具,就用木匠的尺子和铁匠的砧子一点点量。
第一次试射就在兵工厂后面的空地上。周先生亲自扛着用铁管做的“火箭筒”,瞄准十米外的一块钢板。战士们都躲在掩体后面,大气不敢出。“点火!”周先生喊了一声,旁边的助手拉动导火索。“砰”的一声闷响,榴弹没飞出去,反而在射筒里炸了,铁管被炸得弯曲变形,周先生被气浪掀翻在地,脸上蹭满了黑灰,耳朵嗡嗡作响。
“老周!”李明远冲过去扶起他,只见他手上划了道血口子,却咧着嘴笑:“没事没事,至少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射药太多,筒子不结实。”
接下来的一个月,试验成了兵工厂的日常。第二次试射,榴弹飞出去了,却偏了十万八千里,砸在旁边的土坡上;第三次,聚能装药没起爆,榴弹像块石头似的弹了回来;第四次,好不容易打中了钢板,却只炸了个白印,没穿……失败的消息传到部队,有些战士开始嘀咕:“这玩意儿靠谱吗?还不如炸药包来得实在。”
赵刚把这话传给了周先生,老周听了,反而更铆足了劲。他带着人把炸坏的射筒拆开,一点点分析原因,又从天津请来的老钳工那里学了“精密镗孔”的手艺,让射筒的内壁更光滑,减少漏气;聚能装药则反复调整硝石、硫磺和铝粉的比例,光是报废的药块就堆了半间屋。
第五十六次试射那天,天气格外晴朗。周先生新做了一根射筒,用的是从坦克残骸上拆下来的厚壁钢管,榴弹的弹头磨得像个圆锥,顶端还嵌了块铜片——这是他琢磨出来的“药型罩”,能让炸药的能量集中在一点,增强破甲力。
“这次要是再不成,我就去当步兵,抱着炸药包冲!”周先生扛着射筒,手都在抖。李明远按住他的肩膀:“老周,不管成不成,你都是功臣。”
导火索点燃,“嗖”的一声,榴弹拖着一道青烟飞了出去,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精准地撞在二十米外的坦克装甲板上。“轰隆”一声巨响,装甲板被炸开一个拳头大的窟窿,碎片飞溅。
试验所里一片死寂,几秒钟后,爆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周先生扔掉射筒,蹲在地上呜呜地哭了,眼泪混着脸上的黑灰,流成了两道泥沟。战士们冲上来把他举起来,抛向空中,喊着:“周先生万岁!咱有打坦克的家伙了!”
这款被战士们叫做“土火箭”的单兵火箭筒,虽然看着粗糙——铁管上焊着简易的瞄准镜,射时后坐力能把人震个趔趄,有效射程也只有三十米,但对根据地来说,却是划时代的武器。王铁柱抱着火箭筒,对着报废的坦克试射了三,每都能打穿装甲,乐得他把火箭筒扛在肩上,到处炫耀:“以后打坦克,咱不用拼命了!”
二、“飞雷”逞威:火箭筒战惊敌胆
“土火箭”列装部队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传遍了根据地。各部队都来抢着要,最后李明远拍板:每个主力连配两具,由专门挑选的“火箭手”操作,还得经过周先生亲自培训——这玩意儿威力大,操作不当容易出危险。
王铁柱成了全军第一个“火箭手”。他文化不高,但对武器有种天生的敏感,练了三天就掌握了瞄准诀窍,能在二十五米外打中汽油桶。赵刚看着他试射,笑着说:“你小子天生就是玩这个的料,以后就是咱的‘坦克杀手’!”
机会很快来了。九月中旬,日军的一个坦克小队带着一个步兵中队,想偷袭根据地的秋收队伍。情报传到总部时,李明远正在查看火箭筒的生产进度,他当即决定:“让三营上,就用‘土火箭’,给鬼子来个下马威!”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赵刚带着三营在鬼子必经的二道河子设伏。这里两边是陡坡,中间是条窄路,坦克只能一辆辆通过,正好适合火箭筒挥。王铁柱和另一个火箭手张小三,各带着一具火箭筒,埋伏在陡坡上的灌木丛里,枪口对着路口。
上午十点,日军的坦克“轰隆隆”地开过来了,前面两辆开路,后面跟着卡车和步兵。王铁柱趴在地上,透过简易瞄准镜,死死盯着第一辆坦克的侧面——那里装甲最薄,是最佳射击位置。
“等它再靠近点,二十米内再打!”赵刚在旁边低声说。
坦克越来越近,履带碾过石子的声音清晰可闻,车头上的太阳旗晃得人眼晕。王铁柱深吸一口气,手指扣住扳机,瞄准镜里的十字对准了坦克的侧装甲。
“打!”赵刚一声令下。
王铁柱猛地按下射按钮,“嗖”的一声,榴弹呼啸而出,正中坦克侧装甲。“轰隆”一声,装甲被炸开个窟窿,坦克顿时停了下来,冒出黑烟。紧接着,张小三的火箭筒也响了,第二辆坦克的履带被炸开,歪在路边不动了。
后面的日军懵了,他们从没见过这种能在几十米外打穿坦克的武器,还以为是八路军缴获了什么新式大炮。步兵慌忙跳下卡车,想散开掩护,却被陡坡上扔下来的手榴弹炸得人仰马翻。
“冲啊!”赵刚大喊一声,战士们从陡坡上冲下来。王铁柱又装了一榴弹,对着卡在路口的坦克炮塔打了一炮,“轰隆”一声,炮塔被炸开,里面的日军惨叫着滚了出来。
这场仗打得干净利落,不到半小时就结束了。两辆坦克被击毁,三十多个步兵被歼灭,剩下的狼狈逃窜。打扫战场时,战士们围着被炸开的坦克装甲,啧啧称奇:“这‘土火箭’真神了,比炸药包强十倍!”
消息传到日军指挥部,指挥官气得把杯子都摔了。他们实在想不通,装备简陋的八路军,怎么突然有了能打穿坦克的武器。从此,日军的装甲部队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样横冲直撞,每次出动都得派步兵在前面探路,生怕撞上“土火箭”。
火箭筒的用途很快被拓展到打碉堡。黑风口附近有个日军的碉堡,用钢筋混凝土筑成,机枪火力很猛,部队攻了几次都没拿下,还牺牲了不少战士。这次,王铁柱带着火箭筒悄悄摸到碉堡下,对着射击孔打了一榴弹,“轰隆”一声,碉堡的机枪顿时哑巴了,里面的日军被炸死炸伤,战士们趁机冲上去,轻松占领了碉堡。
“这玩意儿不光能打坦克,还能敲碉堡!”王铁柱擦着火箭筒上的硝烟,得意地说。周先生听说后,又对火箭筒做了改进,把榴弹的引信改成延时的,能从碉堡的射击孔钻进去再爆炸,威力更大。
三、重机枪的“轻量化”:铁扫帚横扫骑兵
解决了坦克的威胁,日军的骑兵依然是块心病。虽然用绊马索和炸药雷能对付小股骑兵,但遇到大股冲锋,这些土法子就不够用了。李明远看着骑兵袭扰的报告,眉头拧成了疙瘩:“得有能在骑兵冲到眼前前就把他们打垮的家伙,最好是重机枪,可咱的重机枪太笨重,跟不上骑兵的度。”
当时根据地只有两挺缴获的马克沁重机枪,架在三脚架上,光枪身就有几十斤,还得用水冷却,转移时需要四个人抬,根本没法跟着部队机动。骑兵来袭时,等把重机枪架好,骑兵早就冲过来了。
“要搞轻便的重机枪!”李明远在兵工厂的会议上提出要求,“重量不能过二十斤,不用水冷却,能扛着跑,还得有足够的射,一分钟至少能打三百子弹。”
这个任务落在了机械厂的老王头上。老王是天津兵工厂出身,对枪械构造门儿清。他把马克沁重机枪拆开,研究了三天,摇着头说:“这玩意儿太复杂,轻量化不容易。要不,咱从捷克式轻机枪改?”
捷克式轻机枪是根据地常见的武器,重量轻,能单兵携带,但射慢,威力也不够,打骑兵的马还行,打穿厚点的马鞍子都费劲。老王的想法是:保留捷克式的轻便枪身,换上更粗的枪管,增加射,再把弹匣改成弹链,提高持续火力。
说干就干。老王带着徒弟们,把缴获的捷克式轻机枪拆开,枪管换成从日军重机枪上截下来的,管壁更厚,能承受更高的射;供弹方式改成了五十的弹链,挂在枪身侧面,比弹匣装弹更多;还去掉了多余的零件,把枪身重量从十斤减到了八斤,加上三脚架也才十五斤,一个战士就能扛着跑。
最关键的是解决散热问题。不用水冷却,枪管打不了几十就会烫,甚至变形。老王想了个土办法:在枪管外面套个铜制的散热片,上面钻满小孔,能加快散热;还在枪身上装了个简易的换枪管装置,打热了能在十秒钟内换上备用枪管。
第一挺“冀中造”轻机枪试射那天,老王亲自操作。他抱着机枪,对着百米外的靶子扣动扳机,“哒哒哒”的枪声像炒豆子似的,五十子弹在三秒钟内打完,靶子被打得稀巴烂。连续打了五个弹链,枪管虽然烫,但没变形,换上备用枪管后,还能继续射击。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成了!”老王把机枪递给旁边的战士,“你试试,能不能扛着跑。”战士接过机枪,掂量了一下,扛在肩上跑了个来回,脸不红气不喘:“太轻了!比捷克式还顺手!”
这种被战士们叫做“铁扫帚”的轻机枪,很快列装到各部队的骑兵防御小队。每个小队配两挺,平时由专人扛着,遇到骑兵来袭,能迅架起来,形成交叉火力,射快、火力猛,像一把无形的扫帚,能把冲锋的骑兵扫倒一片。
四、红柳沟的“铁扫帚”:骑兵克星显神威
“铁扫帚”列装后的第一战,就遇上了日军骑兵联队的大规模袭扰。这次,日军学乖了,避开了有绊马索的区域,想从红柳沟突袭根据地的冬储粮仓库。
红柳沟是条开阔的河谷,两边是低矮的土坡,适合骑兵冲锋。负责防守的是新组建的骑兵防御营,营长是以前的神射手老张,营里配了四挺“铁扫帚”轻机枪,还有十个火箭筒小组——李明远特意交代,这次不光要打退骑兵,还要检验新武器的实战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