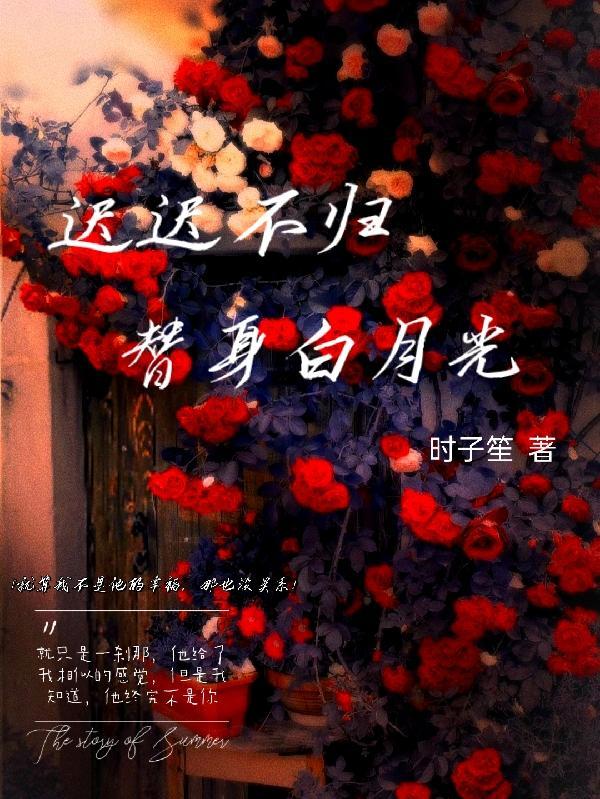乐文小说中文>白荆(郝叔同人) > 第19章(第1页)
第19章(第1页)
白颖的指尖轻触到那道月牙状疤痕,贴着的脸,流下的泪水浸湿了左京的肚皮,她的胃里一阵翻搅。
指尖下的触感并不平整。
作为一名外科医生,白颖摸过无数的伤疤。
阑尾炎手术?老公善意地谎言。
阑尾麦氏点的切口整齐、细小。
而这道疤,边缘呈不规则的锯齿状,那是利刃暴力刺入后、肌肉剧烈收缩造成的撕裂伤。
而且,位置更靠上,更致命。
那是……老公在南非出差的时候……
轰的一声,记忆的闸门被这道疤痕强行撞开。
白颖的眼前瞬间一片猩红,那不是左京的血,而是帝都午后阳光黏稠如蜜的婚房——床头婚纱照如无声嘲讽,空气中弥漫着淫靡的欲望,甜腻却腐朽,像蜂蜜包裹的毒果。
光着身子的李萱诗跪在床边,手中握着郝老狗粗大丑陋的阴茎,另一手倒着黏稠的蜂蜜,紫红色巨大红肿的龟头在阳光下闪着油光。
她笑着,那笑意比毒蛇的信子还要阴冷,舌头舔过蜂蜜,涂抹均匀,像在准备一场祭祀。
“颖颖。”
婆婆的声音柔媚得像地狱里的低语,带着蛊惑的热息。
“教你个乖,你的郝爸爸,最喜欢他的乖儿媳吃他这颗大樱桃了。”
白颖跪在地毯上,赤红的眼睛中透着不可名状的欲望,娇嫩的脸颊充满了病态的潮红,身体似不受控制地麻木。
她抬头,那丑陋的、胀的“樱桃”正对着她的脸,上面沾着李萱诗的唾液,散着腥臊混合蜂蜜的怪味,几乎让她作呕——甜中带腐,像中毒的果实,勾起她体内那股无情感的饥渴火焰。
李萱诗纤长的手指捏住她的下巴,像剥开一层薄皮,让她张开嘴。
“颖颖,含住它,慢慢舔……像吃最甜的果实。”
空气黏腻,蜂蜜的甜腥渗入鼻腔,白颖感到冰凉滑腻的异物抵上唇瓣,接着被强行塞进口腔。
那东西带着令人作呕的腥臊,即使被蜂蜜包裹,也无法掩盖其丑陋和龌龊。
口腔被粗暴地撑开,舌尖被迫触碰那柔软却充满弹性的前端,磨蹭着、吮吸着……
她想吐,喉咙却被堵得死死的,身体深处传来阵阵战栗——那是不可名状的、无任何情感因素的饥渴欲望,像汤汁在体内沸腾,烧灼理智。
就在这时,手机铃声尖锐地响起,像一把凿子,生硬地凿开她麻木的神经。
是左京,是老公的电话。
她浑身一僵,几乎要被嘴里的“樱桃”呛到。
郝老狗没有停下,反而变本加厉,出粗重的喘息,空气如被火燎。
李萱诗笑了,充满魅惑的魔音,藏着暗夜的蛊,低哑如毒藤缠绕耳畔。
“颖颖,妈告诉你一个秘密,郝爸爸最爱的人是你,最喜欢在肏你时,听你和京京通电话。”
李萱诗用纤细的手指轻轻弹了下那颗“大樱桃”,又把头凑到白颖耳边,舔舐着她柔软细腻如脂的耳垂,低语仿佛有蛇信擦过颈侧,带着致命诱惑的温度游走。
“过去你没答应,现在,在你们的婚房,不是更刺激?好好享受吧,和妈一起,颖颖。”
李萱诗温柔地按着她的肩膀,像是在劝她喝下一碗良药
“颖颖,这是命,受着吧。”
李萱诗把手机接通,递到白颖耳边。
左京有点虚弱的声音从听筒传来
“老婆……我没事的……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
白颖一边强忍着嘴里那东西的恶心和屈辱,一边努力平复着剧烈的喘息。
李萱诗轻抚着她的头,亲吻的她的脸颊,舔舐着她修长白皙的脖颈,嘴角露出掩饰不住的笑意。
“老公,今天天气好,我上农户的果园摘了些时鲜樱桃,正在吃樱桃。”
停顿片刻,“老公,对不起啦。面对它,我根本管不住自己的臭嘴,跟你说话,也停不下来——”
李萱诗在旁,一手抓着郝老狗巨大的阴茎,一手托住她的后脑,把龟头重新塞进她的口中,头靠过来,伸出细长的舌头舔着她口外的茎身,也舔到她的唇。
空气甜腥如蜜糖陷阱。
白颖口齿模糊地讲
“老公……我吃……我和妈……一起在吃樱桃呢……”
她出了甜腻的呜咽,那声音带着蜂蜜的假意和嘴里那“樱桃”的腥臊。
“……京京,是妈……”
李萱诗对着手机笑靥如花。
“好儿子,妈嘴馋,看着颖颖吃得真香!妈也吃一个你听。”
李萱诗把阴茎从白颖口中抽出,一口含住,搅动香舌,把吸吮“樱桃”的“咂咂”的声音,通过手机传给了左京。
一根肉柱,一端连接着儿子的嘘寒问暖,一端塞在儿媳的喉咙深处,李萱诗在中间优雅地收割着所有人的对她的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