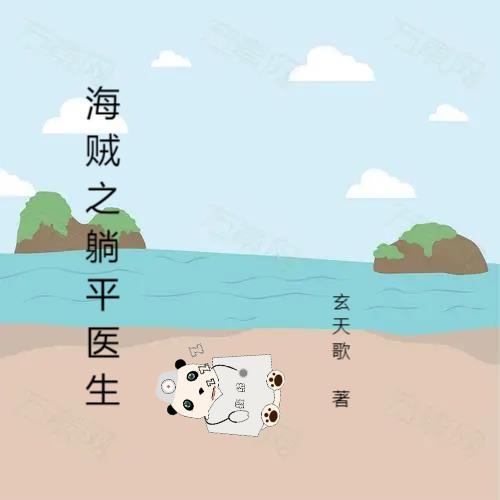乐文小说中文>千山风雪 > 5060(第5页)
5060(第5页)
所有在他此前二十年人生里从未曾有过机会得知的这些滋味,因了她,竟叫他全都知晓了遍。这个李家的女儿,就好像一条虫,一头钻进了他的心里,他自己是再也无法将她驱出去了。
他无法忘记,最初,在知晓她为报信掉头回来了,他赶往风陵的路上,满脑子都是快些见到她,甚至,为了这个目的,他还无耻至极地暗在心里盼望,上天助他,最好叫她被什么事给耽搁住,千万不要那么快便被白四送走离去了。
他没有想到,在他赶到后,她确实如他暗盼的那样,被阻滞了下来,然而,却是以那样一种生死不知的方式。
遍寻她不见,绝望之时,赶到野渡,又误将那个被射死的少年当做是她。那一刻,他唯一的念头,便是他宁愿她已与崔重晏那些人一道,安然踏上了回往青州的路。
那大起大落,此生他不想再来第二遍了。
他将她从那间阴暗的关房里带出之时,她看起来真的就要病死了,肮脏而虚弱,发烧发得不省人事,时而发热,时而发冷。
这三天里,除去白四妻做的一些他实在不便的近身服侍,其余全是他亲力亲为。他一遍遍用洁净的布巾沾水,滋润她发干的唇,慢慢喂她药汁、糖水,她昏迷咽不下去,他便设法让她下腹。他也为她揩去发热的汗,在她因为发冷而蜷起身子的时候,抱住她,伴她同睡,用自己的体热为她取暖。在她感到舒适在他的臂弯里沉沉安眠的时候,他也会忍不住去看她的睡容,无须担心她会因为他的观看恼羞,或是不自在。他只觉越看,越是可爱。世上怎会有如此长在他心窝里的女郎。他恨不能日夜将她搂在怀里,不许她去别的任何地方,只能让他亲她漂亮的眉眼,鼻头,唇瓣,品尝她甜润的舌,再和她做更亲密的事,其余别的任何事情,都不用来烦扰他,他也不用去管了。
有什么关系呢。她其实已经是他娶的妻了,不是吗?甚至,他还忍下他对那条小金蛇的满腹厌恶,当没看见这小畜对自己的敌意,时不时对他作攻击恐吓状,捏着鼻子给它投食、喂水,放它出去溜达,还要盯着,担心它万一就此跑了不回来,他没法给她交待,只因这鬼东西是她的宝贝,他不敢怠慢它半分。
此一刻,他终于等到她醒来,也又一次地失望了。
但他怎么可能还能如前次那样,再对她恶言相向。
堂堂大丈夫,当拿得起,放得下。
世上除了女子,还多的是他裴世瑜应当去做的事。
他认了便是。留不住她,只表明一件事,那便是那边的人和事,羁绊对她更深,他裴世瑜争不过。
“好。”
他俯面,看着她微笑摇头后便垂落下去不肯再与他相望的眼,哑声说道。
言罢,他微微屈身下去,伸臂圈住她的双腿,如抱孩童那样地将她整个人直接抱起,叫她还没有完全恢复力气的双脚离地,身子也都靠在了他的肩上,随即迈步,抱她走了进去。
“但是,你要让我送你回。我将你送到青州之外,我便走,不给你惹麻烦。”
他将她放回到了榻上,看着她,又说道。
“这个,你一定要答应!”
李霓裳吃惊地抬起眼,撞上了他投来的两道目光。他的神情与他方才的语气一样,不容置疑。
对着如此一个为她退让,却又固执的人,她怎可能还摇得动头。
她一动不动。
他沉默地看了她片刻,忽然,轻轻挑了一下眉,显露出轻松的神色,一笑:“那就这样吧,你听我的。”
“你在此安心再养些天,等身体好了,我便送你上路。若有任何放不下的事,你和我说。”
李霓裳一下便想起瑟瑟。
那日她落水后,也不知崔重晏怎样,他回到那个地方,又会如何对待瑟瑟。
见她似有所思,裴世瑜立刻取来文房。
李霓裳隐了自己与崔重晏为是否递送消息而发生的剧烈冲突,也未提他如何对待瑟瑟,只描述了那夜落脚的地方,说瑟瑟从崔重晏那里获悉宇文纵的计划,告诉了自己,她因变故,受伤行动不便,也不知此刻是否还在那个地方,或是怎样的处境。
裴世瑜立刻道:“我这就派人去看,你放心,若是找到,一定也会送她回去的!”说完示意她稍等,走了出去。
李霓裳隐隐听见他和白四的说话声在外响起,片刻后,白四应是去了,他和一个面相和善的妇人一道走了进来。那妇人便是白四之妻,领个婢女,送来了方煎好的药和特意为她准备的饭食。
妇人十分健谈。虽然方才煎药之时,已从少主口里得知李霓裳已醒来,但此刻亲眼看到,还是十分欢喜,先叫李霓裳吃些方熬出来的软粥,还要亲自喂她。
李霓裳忙自己吃了。她在旁看着,等她吃完,又端上药:“不烫也不凉。小娘子快喝了吧。人醒来了就好,再歇息几日,便就能好了。”
李霓裳接药饮了,妇人又端来温水叫她漱口,试探她的体温,忙个不停,想自己昏睡几日,服侍之事,都要她经手,感激她这几日辛劳,要从榻上下去,给她行礼。
白四妻赶忙将她拦住,按她坐了回去,瞟一眼一旁的裴家二郎君,笑道:“小娘子谢错人了。要谢,当谢我家小郎君才对!我所做不多,小娘子昏睡这几日,喂水喂药,全是我家小郎君,他还整夜陪在小娘子的榻前,我叫他去睡,我来换一会儿,他都不放心!”
小郎君送来这少女时,半句没提她身份,但妇人从丈夫口里得知了些情况,又听闻她口不能言,便不难猜知,应是不久前那个将裴家上下之人弄得焦头烂额的青州嫁来的李家公主。
这公主如今与小郎君到底是怎么个关系,夫妻还做不做,她一个下人,自然不清楚。但看小郎君上心的模样,显然对这公主极是在意。他既在意,妇人自然要叫公主知道自家小郎君的心意。
裴世瑜方才回来,白四妻在她身畔服侍吃饭进药,他又回到那张坐床上,手中执一册不知是何的书卷,正歪靠在那里,双目落在书上,耳却都在留意那边,忽然听到白四妻言,转面,赫然见李霓裳也望了过来,眼神中满是羞惭感激,不禁忐忑起来。
他怎敢叫她知道,几次喂药,其实都是他将她扶坐起来,含在自己口里,再一点点慢慢渡送她入腹的。自然,这不是他故意为之,不这样,药汁不好控制,万一呛到她,且大多也会流出她口。吃不下药,她怎能快些好起来。
他固然问心无愧,但万一被她知道,总是不好。
他唯恐白四妻万一再说出什么惹她多想的话,譬如他曾和她同睡一床之类的事,将书一放,起身走了过来,催妇人忙去,说这里有自己。
妇人看向小郎君,他神情庄严。妇人暗笑,便不打扰小夫妇了,收拾东西,和婢女一道退了出去。
李霓裳的感激和羞惭之情却是当真无法言表。
她宁可他如上次分开时那样,冷待乃至痛骂她,骂什么都无妨,她心里反而更自在些。他越待她如此好,她便越觉自己无法回报。
白四妻退出,屋中一阵短暂的静默过后,裴世瑜定了定神,强行解释:“你莫信。她总爱夸大言辞。我也就在旁看护了你一会儿,如此而已。她那样说,反倒显得我好像别有用心。”
李霓裳轻轻咬了咬唇,只会点头了。
他将她乖巧的模样收入眼里,压下心里又涌出的一阵怜爱之情,想起另事,走去取来药膏,坐回到她身旁,恨恨盯一眼此刻正盘身睡在竹筒里的小金蛇,拉来她的伤腕,一面给她卷起衣袖上药,一面道:“此鲸油膏是我阿嫂用最好的料炼的,所得稀少,千金难买,可助收伤口,消去瘢痕。你记得用。”完毕,示意她转脸。
李霓裳一时莫名,却也照他意思,转过脸来,直到看他又挑了一点药膏,要往自己耳朵上抹,这才想起,下意识地躲了一下。
他怎容她躲避,瞥她的神情,手未停,只问:“这里又是如何伤的?看去像是刀划新伤。前次你走时,我记得没有。”
她沉默。他又看她:“是遇到了什么危险吗?”